擺脫中心主義!亞太三年展擊碎歐美當代藝術濾鏡?
地理的“邊緣”,轉化為自由的試驗場,當歐美“中心區”的當代藝術仍在重復既定的語法時,澳大利亞的布里斯班河岸正力圖塑造出自己的模樣,并持續了三十余年...
30年歷史的亞太三年展
如何走自己的路?
當北半球進入冬季的11月,位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亞正以盛夏的序章回應季節的輪回。
這片被大洋隔絕的陸地,常被輕率地貼上“文化沙漠”的標簽。我們對澳大利亞藝術的模糊印象,還僅停留在收藏了3000件中國當代藝術作品的白兔美術館。當然,澳大利亞的當代遠不止于此,他們也有像阿奇·摩爾、艾米麗·卡姆·肯沃瑞、弗雷德·威廉斯、羅恩·穆克等在國際舞臺上大放異彩的藝術家。
三十年間,來自亞太地區的諸多藝術家和策展人都曾登上過這個舞臺。原住民敘事、傳統工藝與當代媒介的交織,使APT形成一種獨特的藝術生態。


如今,亞太當代藝術三年展已步入第十一屆。
像往年一樣,它的發生地仍是在布里斯班昆士蘭美術館與現代藝術館(QAGOMA)。這屆以“The Momentum of the Future”(未來的動力)為主題,集結了來自澳大利亞、新西蘭、日本、泰國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亞等30個國家的70位藝術家及藝術團體,作品超過500件。
既有強烈視覺沖擊力的大型裝置,也有情感表達細膩的微小敘事。策展團隊巧妙地掌控著展陳節奏,張弛有度。無論對業內人士還是大眾而言,觀展體驗都相當友好。
每一屆三年展中均會呈現地標性的巨型藝術裝置。這次全場C位留給了泰國藝術家Jai Inn,他借鑒了隧道、卷軸和懸吊圖騰的結構,呈現三件精心編排的大型裝置。
天地水汽、繁花風動,藝術家通過這些大型裝置作品,創造了層次分明的視角,重構空間秩序。隧道將觀眾從開闊空間逼入狹窄通道,以物理介入方式,質疑美術館作為“藝術圣殿”的霸權屬性;透光畫布通過縫隙形成“可穿透的界面”,重新評估架上繪畫現已成為商品的問題。

閃爍的屏幕影像、細膩的樹皮畫以及層層疊疊的大型裝置構成的神秘符號與柔軟線條,APT11觸及了家園文化、勞動力遷移、原住民藝術等多重熱門議題。

作為移民國家,澳大利亞通過亞太三年展持續推動本土與國際觀眾的文化互動。
自1993年創辦以來,累計吸引了全球游客近500萬人次,昆士蘭美術館館藏中已收錄約1400件歷屆參展作品,形成亞太地區當代藝術的重要文獻庫。
依舊稀缺的中國面孔
尋找中國面孔,是我去看國際大展時的本能反應。
遺憾的是這屆APT,中國藝術家沒有以往的占比大,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是80后藝術家王拓的影像作品《第二次審問》。該作品大膽觸及了本土語境中鮮少觸碰的敏感議題:審查制度、體制框架、國家命運、歷史規律與社會變革。
來自中國香港,出生于1956年的藝術家楊東龍,擅長發現并捕捉城市中被人們忽視的細節。他運用多角度觀察,以精細、風趣且充滿活力的寫實筆觸,在流暢的畫面中勾勒出城市與人物的生動形象。
《360°+》(2021-2023)作為一組包含18件作品的大型油畫裝置,靈感來源于藝術家位于港島西堅尼地城附近工作室的周邊景觀。該系列以四幅連貫的長卷軸式全景圖為核心,輔以14件獨立畫作,展現了疫情中靜謐詭異的城市。
最近這些年,我們幾乎已經習慣了中國面孔在國際舞臺的缺席,無論是威尼斯雙年展,或是巴塞爾藝博會,零星的露出幾乎是常態。但一個主打地域特色的三年展卻依然繞開了中國,原因何在?最近這些年,我們幾乎已經習慣了中國面孔在國際舞臺的缺席,無論是威尼斯雙年展,或是巴塞爾藝博會,零星的露出幾乎是常態。但一個主打地域特色的三年展卻依然繞開了中國,原因何在?
APT亞洲當代藝術策展人魯本·基汗(Reuben Keehan)給出的解釋是:“本次APT未能如往常一樣呈現大量中國作品,主要原因是籌備期間疫情導致的交通限制,使我們無法順利推進相關工作。盡管如此,我們仍通過其他形式生動展示了中國藝術家的作品。在下一屆APT的調研中,中國將成為我們的首選地。”

相比今年的低調,中國藝術家在APT也曾有過頻繁亮相的時刻,甚至多次在APT核心展區中以中國藝術家作品作為主要陳列及展示。
1999年,蔡國強帶著他的大型裝置《過橋》進入第三屆亞太三年展,橫跨主展區Watermall,當游客成功通過中心點時,會被一縷細霧迷住。2013年,他又以昆士蘭景觀為靈感,為展覽“歸去來兮(Falling Back to Earth)”創作了壯觀的裝置作品。
2012年,藝術家黃永砯展出了一件名為《彈簧》(Ressort)的作品,這是一條長達50米的鋁制蛇骨。在法語中,"Ressort"有多重含義:彈簧、一種可修復的能力、一種能量,這些含義都與這條蛇蜿蜒盤旋的動態形態相呼應。
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還有艾未未的著名水晶吊燈《回旋鏢(BOOMERANG)》(第五屆亞太三年展)、中國藝術家邱志杰的壁畫《技術倫理地圖》(第九屆亞太三年展)等。

原住民到AI,
人性是否會被技術吞噬?
“當然我們的討論始終圍繞著亞太地區的當代藝術,深入剖析這一區域紛繁復雜的文化景觀、歷史脈絡、發展進程及其影響力。我們專注于那些既契合當下、又能映射時代變遷的藝術創作。”第十一屆APT主策展人塔倫·納格什(Tarun Nagesh)解釋了作品的選擇標準。

在原住民敘事與離散文化的在地轉譯中,澳大利亞原住民D Harding將羊毛氈裝置融入在地敘事,致敬祖先的負鼠皮斗篷傳統;菲律賓原住民藝術團體Kikik Kollektive以神話及反殖民敘事壁畫紀念菲律賓革命英雄;巴勒斯坦裔藝術家Dana Awartani的裝置藝術作品《廢墟旁佇立(Standing by the Ruins)》也格外突出。
在充滿詩意又傷痕累累的悲壯之地中東,藝術家Dana Awartani采用手工打造的土坯磚。
這些磚塊以三種不同的土壤色調精心燒制,形成了精致的圖案。簡單的阿多比磚蘊含了多個面向的意義解讀,它們交錯跳躍、彼此延伸,最終指向同一個永恒與無限。
原住民藝術以手工的溫度觸動著觀眾,而數字藝術則以前沿的技術冷光引發反思,二者在展覽中形成強烈對比,卻又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問題:我們如何在快速變化的世界中保持人性的溫度。
新加坡藝術家Dawn NG通過冰凍顏料融化過程的影像,捕捉時間的流逝與物質的脆弱性。印度藝術家Rithika Merchant利用數字技術描繪未來星球生態,傳統水彩與數字拼貼結合,反思家園環境危機。
海報作品《The Machine Ghost in the Human Shell》則出自泰國行為藝術家Kawita Vatanyankur與美國藝術家Pat Pataranutaporn攜手打造的影像藝術。通過全息投影與AI操控,藝術家身體成為機器與意識的戰場。
表演中,AI以電子脈沖支配肢體運動,而藝術家通過精神抵抗展現“肉身牢籠”的困境。作品直指泰國與印度勞工剝削問題,質問數字時代“人類是否仍是思想的主體”。

藤編的韌性、染織的呼吸、陶土的溫度,原住民藝術家以樹皮作畫,太平洋島民將貝幣串成數字時代的密碼……
盡管各類國際三/雙年展的議題大同小異,但在作品選擇上,我能看到策展團隊的用心,以及對實驗探索內核的堅持。
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撕扯
盡管APT試圖呈現多元視角,但在有限的展覽空間和時間內,難以全面覆蓋亞太地區所有文化語境,部分地區的表達甚至被納入一種“泛亞太”的敘事框架中。
而原住民及少數族裔作品鋪天蓋地的呈現仿佛深陷“政治正確”的窠臼,是為了迎合對“異域風情”的想象,而淪為“他者文化”的符號?
聚焦殖民歷史、勞工、文化遺產等議題的作品略有些泛濫,令觀眾倍感壓抑。這類作品似乎態度有余,力道不足,看多了還有些膩。
新西蘭毛利藝術家Brett Graham帶來了四件力作,宏偉的雕塑手法揭示了殖民時期對毛利族資源的剝削。盡管作品在流動性、短暫性和與家園分離的主題上充滿了批判的鋒芒,但在展現毛利文化時使用的傳統符號與宏大敘事,容易讓觀眾產生疲勞,視覺呈現并不理想。
挑剔的觀眾免不了對國際大展擺出一副既要又要還要的姿態:既展現文化的多樣性,又避免簡化為符號;既回應歷史的沉重,又要傳遞未來的希望;既融入全球語境,又保持本土的獨特性。
布里斯班作為澳大利亞的“非中心城市”,天然的邊緣性賦予了它獨特的自由與可能性。在這里,藝術與文化不受中心城市的束縛,反而能夠以一種更加實驗性、更加本土化的方式恣意生長。

APT聚焦本土藝術家、深刻回應區域性的獨特議題。
在這場視覺盛宴背后,對這個陌生的三年展仍有太多的好奇。2月初,我在APT11的展覽現場與昆士蘭美術館與現代藝術館(QAGOMA)亞洲及太平洋藝術策展總監塔倫·納格什(Tarun Nagesh)及亞洲當代藝術策展人魯本·基汗(Reuben Keehan)進行了一次面對面的交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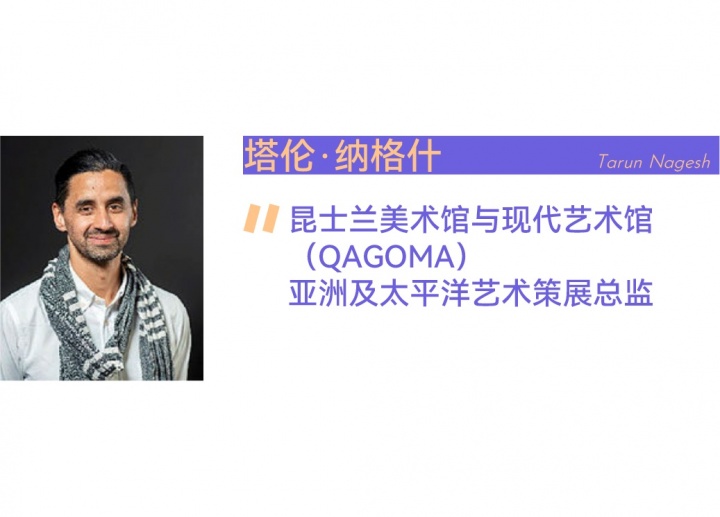

Hi藝術(以下簡寫為Hi):藝術家的篩選準則及其在策展理念中的具體體現?
塔倫·納格什Tarun Nagesh(以下簡寫為TN):自上一屆三年展以來,某些區域或群體在聚光燈下的缺席,促使我們以更謙遜的姿態投入持續的學習與勘探——這不僅是對地理盲區的補足,更是對認知框架的重構。
當文化注意力在特定區域過度聚集時,我們選擇將目光投向未被充分言說的地帶。這并非對既有成就的否定,而是為下一屆展覽預留的開放性生長空間。我們致力于構建更具包容性的認知框架——一個刻意與歐美藝術史譜系保持對話距離的平行系統。
每屆展覽都是多重對話的交響:策展團隊內部關于作品選擇與呈現方式的思辨,與亞太地區創作者、社群守護者、文化實踐者的深度碰撞,以及展場空間與觀眾之間的能量交換。我們清醒地拒絕對作品施加西方美學的濾鏡,轉而通過在地化的對話,讓作品自身攜帶的文化密碼激活我們的感知系統。

TN:亞太三年展(APT)辦了三十多年,為全球文化交流做了不少貢獻。展覽一直在嘗試新形式,跟著時代變化。博物館和藝術圈也在變,特別是90年代,APT從現代主義轉向當代藝術,努力擺脫歐美中心,走自己的路。那時候,亞太地區經歷了很多社會和政治變化,APT展示了這些變化中的藝術家作品,影響挺大。
到了21世紀初,藝術市場火了,但亞太地區在國際展覽里還是不太顯眼,還有很多事要做。澳大利亞在連接亞太藝術對話上有獨特優勢,但我們的藝術觀念受歐洲影響比較大,可能不太適合理解亞太藝術。APT給藝術家提供了一個平臺,既尊重傳統,又挑戰傳統,展現了藝術的多樣性和社會意義。2032年布里斯班將成為夏季奧運會舉辦城市,期待未來。
但現在,當代藝術吸引了大量觀眾,成了最受歡迎的藝術形式之一。它的魅力就在于“當代”二字,大家都想看看現在發生了什么。我覺得APT在推廣當代藝術上起了很大作用,培養了一群忠實的觀眾。年輕人從小接觸藝術中心的兒童項目,長大后還能回憶起那些難忘的作品對他們的成長影響很大。
另一個挑戰是引入歐洲以外的藝術。以前在歐美,美術館幾乎是唯一能看到這類藝術的地方,展示亞太當代藝術更是難上加難。但現在已經很常見了。以前很少碰當代藝術的大型機構,現在大部分時間都在展示它。
觀眾數量的增長讓我覺得,大家對我們展示的內容越來越信任,愿意冒險去探索那些可能一時看不懂的作品。我覺得這標志著一代人的轉變,特別重要。它帶來了很多機會,也讓我們意識到,藝術家和作品本身就能和觀眾建立深刻的聯系,不需要我們過多引導。

RK:澳大利亞藝術生態很獨特,科學、藝術、心理學跨界融合,催生了很多風格多樣的藝術家。原住民藝術特別重要,在展覽和市場里都很搶眼。
不過,澳大利亞藝術在國際上還不夠火。原住民和本土藝術家的作品在國際市場占比小,頂級藝術家名單里也少見他們的名字。主要是地理距離遠、運輸成本高,還有本地市場自給自足,藝術家和國際互動少,導致國際知名度不高。
總的來說,澳大利亞藝術很有特色,但怎么打破地理限制,提升國際影響力,依然還面臨挑戰。
Hi:本地的白兔美術館是全球最大的收藏中國當代藝術的國際美術館,如何評價其在澳大利亞當地的影響?
TN:我第一次聽說白兔美術館 (White Rabbit Gallery) 的時候特別興奮。參觀了幾次后,真的被中國當代藝術的豐富和深度震撼到了。這不僅說明中國當代藝術很重要,全球都在關注,更傳遞了一個信號: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。
在澳大利亞,私人博物館不多,大部分是大博物館,所以這種展覽特別難得。它能給觀眾帶來不一樣的視角,展示藝術背后的運作模式。我覺得,如果這些畫廊能和公共機構合作,那就更好了。觀眾可以近距離接觸這些作品,甚至發現藝術家在其他地方的作品,這對大家來說是個特別好的機會,能體驗到各種各樣的藝術風格。

白兔美術館,2025
RK:現今的大型展覽面臨多重挑戰,包括成本、可持續性以及如何真正服務受眾等問題。盡管困難重重,我們仍肩負責任,確保展覽引發深刻思考并傳遞價值。全球許多地區尚未參與國際藝術展覽,這要求我們以正直態度應對,而非僅追求“異國情調”的表象。
展覽必須明確其服務對象——無論是代表當地社區,還是以負責任的方式呈現文化政策。城市與國家當局需不斷反思展覽的相關性與意義,尤其是在與合作伙伴和受眾互動時。未來,大型展覽的核心問題在于如何將展覽內容與參觀者體驗深度融合。這不僅關乎藝術表達,更是活動組織者必須深思的基本命題: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,讓展覽既具深度,又能真正觸達人心。
 微信號:hiartmimi
(可享會員福利)
微信號:hiartmimi
(可享會員福利)